DNA小说 > 女生 > 不要爱上她最新章节列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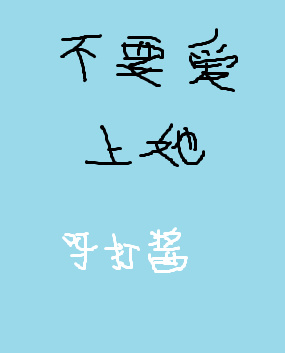
不要爱上她
- 内容简介:
- 预收文《我的欧几里得》↓这里是南美洲。有极致美景、却也枪.支肆虐、毒.枭横行。殷悦觉得自己脑子有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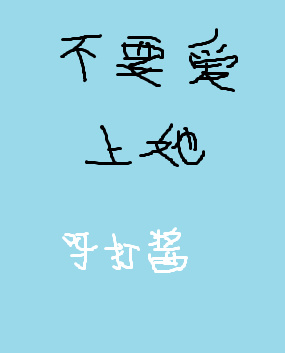
下个月的时候,陈简的月经没有如期而至,只是她食欲不错,头脑清晰,睡眠质量好得很,便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那天晚上,她回到房里,摁开了灯,去换干净薄薄的衫子。她□□了上身坐在床上,耳边嗡嗡,她手抓上浸泡过药水的蚊帐,别开一道口,把苍蝇放了出去,又扎紧,她垂眸,望见自己结实饱满的乳.房,微微胀痛,乳.头有很明显的色素沉着。 她到底留了个心眼。 这个地方是找寻不到试纸的。下一个休整日的时候,她整理包裹,带上伞和钱包,借乘了粮食署的顺风车,去了一趟当地繁华市区最好的医院。 陈简坐在一排挺着圆肚,扎鲜亮彩色头巾戴大耳饰的黑人妇女中间,一言不发。她想起以前他们在海滨边度假,他们把涂抹了膏霜的肉体在阳光下晒得温暖,又去彩色的大棚子下吃牡蛎。承钰给她剥,她说我的手废掉了,他就喂给她,她去咬去衔,吸一口,汁水没兜住,流下来,她就笑嘻嘻地用湿淋淋的嘴巴亲他的脸。他嫌弃地抽了纸巾去给她擦脸,她像灵巧地麋鹿一样跳起来,去闪去躲,跳到他身后,扑上他的肩膀。她赶他走,他说我的双腿废掉了,她就说问那怎么办呀,他说你亲我一下给我加油好了,她每亲他一下,他就慢吞吞地走一步,她哈哈大笑,捧着他一顿乱咬,说现在你可以一口气走到阿拉斯加啦。晚上的时候,他们住在建在海上的木屋...